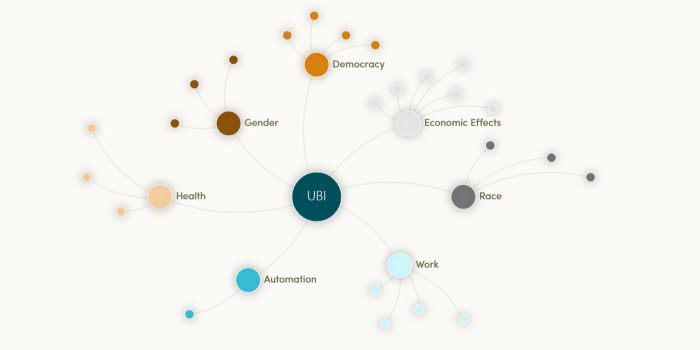作者:Stanford Basic Income Lab
译者:赵岩
原文链接:<https://basicincome.stanford.edu/research/ubi-visualization/>
民主
公民参与
本节讨论UBI如何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特别是选民投票率。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参与一个社区的政治生活的过程。参与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投票、志愿服务和竞选活动等等。下面的摘要首先探讨了UBI对公民整体参与的潜在影响。然后,它将重点缩小到低收入公民,历史上他们的参与率很低。尽管UBI有望增加公民参与度,但验证据缺乏且不确定。
一些民主理论家认为公民参与是民主成功运作的关键(Skocpol & Fiorina, 2004)。他们担心以投票率下降和志愿者组织或工会等公民团体存在的减少等形式的公民参与率的降低。参与减少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对就业公民的时间限制增加。事实上,有一些证据表明,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一直在增加(《经济学人》,2014)。对于美国公民协会数量下降的另一个潜在解释是,上层和中产阶级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增加,她们在前几代人的无偿劳动可能对美国公民生活的稳固性至关重要(Putnam, 2001)。
如果UBI影响劳动力参与,例如通过减少正式劳动时间,它可能会腾出公民参与公民活动的时间。有一些证据表明,UBI将使个人能够将花在工作上的时间用于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其他活动,如教育或抚养孩子。UBI是否会提高中高收入公民的公民参与,还有待实证调查。
民主理论家主要担心的是低收入公民的参与,他们的参与水平从一开始就一直不高。有大量文献表明,政治参与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相关性(Ojeda, 2018)。特别是,一个人投票的可能性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选民投票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Akee et.al,2018;Scholzman et.al ,2018)。收入对参与的影响是曲线的,这意味着收入对投票率的影响在收入分配的低端最大(Ojeda, 2018;Rosenstone & Hansen,2009)。在政治学文献中,已经阐明了这一现象的四种因果机制。首先,低收入家庭可能缺乏参与所需的技能和资源(Scholzman et.al,2018);其次,运动和其他组织的动员努力往往忽视低收入社区(Rosenstone & Hansen, 2009);第三,政策议程不强调与他们相关的问题(Piven & Cloward, 1988);第四,选民身份法或重罪剥夺公民权等限制可能不成比例地影响低收入公民(Hershey, 2009)。
UBI可以解决其中一些因果机制,从而提高参与度。如果低收入公民因为经济障碍而没有参加选举,比如在选举日无法请假或找不到托儿服务,那么一个重要的UBI将有助于增加参与选举的机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UBI可能是一个对低收入公民具有直接意义的政策问题,这反过来可能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容易动员的选民阶层,类似于社会保障立法的通过导致老年公民作为一个政治阶层的出现(Campbell, 2011)。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摆脱贫困的人的子女更有可能投票(Akee et.al ,2018),这表明强大的UBI可能对政治参与产生长期影响。
但是,尽管UBI会消除一些经济障碍,但它可能不会消除语言、政治知识甚至兴趣方面的障碍。因此,UBI作为解决公民参与度低和不平等问题的办法,可能影响有限。此外,包括削减公共教育等其他重要服务的UBI提案版本,实际上可能会对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不是促进参与率。当然,UBI也不太可能影响到参与的制度性障碍,比如旨在限制选举权的法律。
民主化
本节讨论UBI如何可能导致政治机构之外的生活领域(如工作场所或家庭)的民主化。
民主化是使某一事物——一个政权、一种文化或一个决策过程——更加“民主”的过程,也就是说,更能反映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民主化的一种方式是增加民主制度(如投票)的使用。但也可以通过民主化来提高人的能力。例如,让人们更了解他们投票支持的政策类型。
当民主理论家考虑UBI的潜力时,他们对这种类型的民主化特别感兴趣(Goodhart, 2008;Pateman,2004)。民主理论家经常担心经济依赖对民主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私人领域受到依赖的个人,在公共领域可能更容易受到胁迫。一个专制的雇主或丈夫可以控制一个人如何投票或捐多少钱。然而,依赖性还会以一些更微妙的方式影响一个人践行公民身份的方式。例如,如果一个人花太多时间工作或为上级服务,他们可能会被阻止进行有效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思考和教育。依赖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使一个人更“奴性”,更不愿意独立思考。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也在20世纪中期写道,工人——那些依靠资本家维持生存的人——“在许多方面……对构成自由社会驱动力的许多东西都是陌生的和有害的”(Hayek,2010)。
就UBI减轻经济依赖而言,它可能有助于减少这一问题。这种想法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独立,那么他在政治上也更有可能独立。不过,这种说法的经验证据非常不确定。尽管理论家们假设经济依赖对一个人的民主性格有负面影响,但通过UBI等计划增加经济安全的效果尚未得到衡量。造成“坏”民主品格的原因还有很多,或许更重要,比如媒体的错误信息或意识形态隔离。此外,雇主对政治参与施加压力已经是非法的,可能不会普遍存在。
有一些有限的证据表明,UBI可能会导致个人参与可能使他们成为更独立公民的活动。例如,有一些证据表明,接受基本收入的年轻人用教育取代了劳动力参与(McDonald & Stephenson, 1979)。如果增加教育——或者其他替代工作的活动——能把个人变成更好的公民,那么UBI至少可以间接地对民主化产生积极影响。
经济依赖令人担忧,因为它可能会让一些人受恶意行为者的摆布,如坏老板或专横的家庭成员,但民主理论家在提高人们参与民主制度的能力方面也有其他考虑。即使没有个人不良行为,例如,一个机构的首要方法是结构化可以影响的个人习惯。专制制度可能会导致个人发展出顺从的性格(Pateman, 2004)。如果家庭和工作场所是不平等的,人们会形成一种习惯使他们无法有效参与民主国家。
UBI的支持者认为,只要转移的规模足够大,该政策就会产生民主化效果(Pateman, 2004)。通过使人们能够选择是否工作和为谁工作,并增加他们的退出选择,基本收入可能会阻止个人签订不民主或不平等的合同。当个别人有更多的经济安全,不民主的机构可以从内部重塑和重新设计变得更加民主:工作场所和家庭可以变得更加平等,工人和家庭成员可能会更容易拥有自主决策所需的美德。
不过,这些积极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经济独立是否真的会导致工人选择他们可以实践民主美德的工作场所,或者退出的威胁是否会迫使雇主改革其内部治理结构。不过,还是有一些有希望的预示。在印度中央邦进行的基本收入实验产生了关于集体劳动增加的轶事证据,描述了新生的工人集体劳动。此外,个人从雇佣劳动到“自营”工作(即为自己的利益而做的工作)的显著转变(SEWA Bharat, 2014)。如果成为“自己的老板”会灌输或发扬民主美德,那么这样的转变不仅会增强个人的权能,也会对政体有益。至于使家庭更加平等,有证据表明,现金转移确实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们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和/或赋予她们在家庭决策中更大的权力(SEWA Bharat, 2014)。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民主化”家庭(Pateman, 2004)。
但我们可能有理由质疑UBI能否以其支持者提出的方式实现民主化。UBI的反对者认为,它可能提供经济独立性,但不会导致工作场所的民主化改革(Gourevitch, 2016)。他们特别认为,对于有工具理性工作的个人来说,基本收入只会减少工作场所的权力不对称–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因为依赖其收入而工作的个人来说。但是个人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例如,他们可能取决于职位的意义或社会联系。这些员工可能会被禁锢在专制的工作场所,因为仅仅是“退出的自由”并不一定会带来其他令人满意的机会。更普遍地说,民主改革并不必然从“退出权”的逻辑出发。由于UBI将工人视为独立的市场参与者,它可能会降低工人集体组织的能力,减少他们进入特定民主途径的机会,降低他们改革组织的能力。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UBI与工作场所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全民基本收入的民主正当性
本节解释民主理论家如何试图为UBI辩护。
UBI的支持者提出的一个论点是,生存和政治参与一样,是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学者们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两种论证。第一个是关于UBI的工具价值。它试图证明权利是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与经济独立有关的权利的平等保护,有关政治参与的权利(如选举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就无法维持。因此,UBI对于支持其他民主权利是必要的。第二个论点涉及UBI的内在价值。这一论点在生存权和选举权之间做了类比,声称两者都是民主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在这种范式下,反对全民基本收入就像反对普选一样,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反民主的。
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集体角度来看,UBI都被视为对各种民主权利具有工具价值。从个人角度来看,最常见的论点是权利是相互交织的:对任何特定权利的侵犯也会损害其他权利。例如,没有集会自由,一个人就不能实行宗教自由(Shue, 1996)。这一主张的支持者认为,对他们所认为的一个人的经济权利的侵犯会导致对其他政治权利的侵犯。例如,言论自由如果破坏了你的经济依赖,意味着你和你的老板不能表达政治分歧。因此,UBI作为一种经济权利很可能保护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至少在它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可以给予真正的退出选择(Goodhart, 2008)。
较少有人争论的是,UBI在集体提供权利方面可以发挥工具性作用。一些基本的民主权利依赖于所谓的“参与性资源”(Scholzman et al., 2018)。例如,投票需要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选举需要投票站、投票软件、投票站、登记和登记协助以及其他后勤资源,如往返投票站路线上的道路和交通管理。一些国家甚至规定选举日为法定假日。在这个框架中,UBI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消除了参与的经济障碍,还在于它如何积极和集体地为提供参与所需的资源做出贡献:时间、金钱和动机。
一些理论家认为UBI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它促进了政治权利,还因为他们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权利(Pateman,2004)——类似于投票。虽然关于投票为何有价值有许多工具性的论据——更好的政策结果或追究民选官员的责任——但许多民主理论家认为,投票也具有内在的价值。投票,这个观点认为,是一个象征性的政治平等;即使人们没有平均参与,但普遍可及的事实本身就表明,民主是由所有人统治,为所有人服务的(Chapman, 2019)。全民基本收入的内在理由是相似的。即使UBI没有被证明能增加人们的选举参与或其他权利的使用,一些学者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因为它象征性地展示了平等的公共地位——一个政体中的所有个人都被同等重视,并被认为是公共生活的平等参与者(Pateman, 2004)。
良好的治理
本节探讨UBI如何改善民主国家的治理,特别是通过研究UBI如何影响民主问责制和合法性。
作为一种政体类型,民主往往因某些内在特征而受到重视,例如它如何体现公民平等。但是,重视民主也有工具性的原因,包括民主可能带来更好的治理。与其他形式的政府相比,民主可能既更合法,也更负责,从而产生对公民更有利的政策。如果民主不能负责或合法——也就是说,不能体现这些善治的价值——它可能会导致对民主的不满和对替代政体类型的渴望。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运作方式的不满正在上升;在27个国家调查,平均51%的人不满意当前运作的民主国家(Richard Wike et al ., 2019)。那些认为自己的政府不负责任(腐败或无法提高生活水平)或非法(不值得信任或不愿尊重基本权利)的人更有可能不满。
如果我们重视民主是因为它与良好治理的联系,我们可能会问UBI对民主国家良好治理的能力有什么影响。来自现金转移支付的证据提供了关于问责制和合法性的见解,这两种价值观被认为是善治所必需的。
UBI将如何影响公民向政府问责的能力?就UBI可能提高选民投票率或公民参与度而言,它很可能会增加政府的问责制。然而,仅仅公民参与是不够的;为了确保良好的治理,如何参与也很重要。“不健康的”政治参与,即公民以提供私人物品为基础来选择和制裁领导人,会损害国家的治理能力(Khemani, 2015)。例如,不健康的公民参与可以在特殊利益集团中看到,他们动员起来,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从政策中获取利益。当公民根据领导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来选择和制裁他们时,公民参与就是“健康的”。
UBI既是一种公共产品,也是一种私人产品,它使健康与不健康公民参与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一方面,减少经济依赖性可能赋予公民监督政府和选举响应公民呼声的领导。然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证据表明,也有一些情况下,该政策可能会降低选民的独立性,使他们更有可能投票给现任者(Baez et al., 2012)。投票过程提供礼物或钱换票就极大可能与各国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有关(World Bank, 2016)。如果政客们利用UBI的直接好处来“收买”选票(例如,通过承诺增加薪酬),这可能会阻碍公民在其他违规情况下罢免这些领导人的能力。然而,UBI的普遍性有可能减轻这种影响;即使是收入更高的公民也能获得这种福利,这一事实可能会阻止“柯利效应”的出现,即政治家通过提供扭曲性福利的政策来增加其政治基础的规模,以确保连任(Glaeser & Shleifer, 2002)。
关于UBI和问责制的一个相关担忧是,选民对UBI的兴趣可能超过对公共利益的其他重要关切。例如,一些人认为,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年度股息“扭曲”了当地政治,因为居民投票保护他们的个人支付,损害了学校和大学等公共服务(Sundlee, 2019)。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政策提供有针对性的福利时,就像现金转移所做的那样,其他类型的服务,如公共卫生或教育,可能往往会有更少的资源可用(Khemani, 2019)。然而,证据是混合的,因为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选民愿意考虑限制他们的永久基金股息支付或将永久基金的额外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和项目(Stalzer, 2015)。要了解UBI与选民对公共品提供的兴趣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很大一部分政府合法的知觉依赖于公民认为政府是负责任的。因此,就UBI增加民主问责制而言,它也将增加民主的合法性。但民主合法性的另一个轴是社会凝聚力,这在一些学术工作中也被称为社会资本或社会连通性。
社会凝聚力在实证研究确实影响健康的民主国家,因为它通常与改善机构的性能,经济繁荣,增加动员参与度,和一般意义上的公民功效有关。(Campbell,2013;Putnam et al., 1994;Rosenstone & Hansen,2009)。实证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如收入高度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如各种社会职位存在不平等的报酬和机会)会对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Khambule & Siswana, 2017;Vergolini, 2011;Wilkinso,1997)。就UBI可能减少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而言,它可能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
UBI可能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另一种方式是改变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如果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与他人接触的活动,比如接受教育或参加志愿者工作,他们可能会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凝聚力。但UBI也可能对社会凝聚力产生负面影响。UBI的接受者可能会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或他们已经拥有的网络上,这可能会降低社会凝聚力。因此,由于没有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获得UBI,他们可能会参与哪些类型的活动,因此很难估计它可能对社会凝聚力产生的影响。此外,有人认为,工作场所在民主国家发挥着关键的整合作用;经济需要迫使不同背景和种族的人一起工作,这种日常互动使他们建立跨越社会分裂的个人联系,并实践合作和共识的技能(Estlund, 2003)。如果UBI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与那些他们本来不会选择交往的人合作,那么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降低社会凝聚力,从而对社会凝聚力和民主合法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UBI对社会凝聚力的潜在影响是高度可变的,而且缺乏证据来支持任何一个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UBI还可能影响公民对国家的信任,这是民主合法性的另一个轴心。真正普遍的基本收入创造了一种服务,从最贫困的公民到最富裕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公民对政府服务的持续参与可能有助于提高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法性,特别是当这些服务被认为特别重要或有能力时。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表明,转移支付受惠者对核心国家机构、地方政府和在职行为者的信任增强了(Layton et al.,2017)。坦桑尼亚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有条件现金转移显著提高了对民选领导人的信任,同时提高了人们对政府回应公民关切的感知,以及对领导人诚实的感知(Evans et al., 2018)。然而,在这项试验中,现金转移部分是通过民选官员的亲自监督来实施的,并以获得其他服务为条件,如医疗保健。有可能对合法性的一些影响是公民与政府直接互动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线UBI实际上可能会降低社会信任,因为公民与各种政府官僚机构的接触会减少。
可能不必要的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个人接触有增加的合理性,但是足够能力的数字化或在线服务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事实上,在线UBI甚至可能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因为它消除了服务提供中腐败和微观统治的一些可能性。首先,这种UBI缩短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链条”;将资金必须经过的“手”移开,可以提高透明度,减少腐败(World Bank, 2003)。第二,它可以使服务提供更加公平。“街头”官僚,那些站在服务提供前沿的人,可能会被接受者武断地认为决定谁能以什么理由和何时获得福利方面。消除个人互动中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元素实际上可能会改善公民与政府的互动,UBI的净影响可能是增加民主信任。芬兰基本收入实验的初步结果支持了这样的结论,因为那里的研究人员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基本收入接受者对政治家和法律体系的信任有了小幅但显著的提高(Kangas et al., 2019)。经济不平等的平等化可能也促成了这种效应;因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是由其他公民提供服务的,微观统治削弱了社会信任和政治共同体的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如果微观统治更有可能影响低收入公民,那么不平等的减少可能会使其他形式的服务——从教育到医疗保健——看起来更公平,国家本身也更合法。
转载请注明:《中国社会分红/基本收入研究网》 浏览量:403 views